UID244238
威望239
金钱82839
交易诚信度0
主题57
帖子996
注册时间2006-4-4
最后登录2024-10-2
核心会员
      
交易诚信度0
注册时间2006-4-4
|
马上注册 家电论坛,众多有奖活动等你来参与!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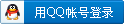
x
既然是“说开去”,难免东拉西扯,如果朋友以为我说话离题,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对许多中国听众,尤其是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喜欢柴科夫斯基似乎比喜欢巴赫更为容易一些。巴赫是睿智的,其音乐充满理性的光辉;柴科夫斯基是多情的,其音乐包含着痛苦的人生体验。
从更深层的原因分析,几千年来,普通中国人在自然灾害、强权统治、贫困窘迫面前,在物质贫乏和精神压制的无奈之中,逐渐学会了乐天知命,随遇而安。但在内心深处,却也形成了一种悲情气质。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金榜提名,是几千年来不变的梦想。但无论是状元及第还是名落孙山,结局大都不好。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迫害达到登峰造极程度。因而柴科夫斯基极具悲情色彩的音乐,很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在我们的一些有关音乐或者其他论述中,常常有意无意地从作者家庭、生长环境“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这未免失之于绝对。有的学者把柴科夫斯基的悲情气质归结为其自身的原因,如他家人的精神病史、他本人的同性恋苦恼、婚姻失败等等,因为这些原因,才使他极具多愁善感的天性。我一直觉得这种看法过于片面甚至缺乏厚道。当我们对历史上的不朽人物的心理或精神方面的缺憾从遗传去解释时,我们对他已经不可能仰视如高山、如繁星。现在不提血统论了,却又喜欢从遗传角度去解释。强调中庸的国度,从古到今却一直走极端。我想到我国百岁教育家魏寿昆,幸好魏老先生一生也没闹过精神性疾病,否则肯定又有人说是遗传,因为魏老的父亲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国外学者论及家庭、环境的背景,但并不从中直接得出结论。这也是中外学者的差别之一。当然,我并不否认个人际遇、家庭环境对一个人性格、心理的影响,但这只能作为一个原因考虑,而不一定是决定性因素,人的社会环境是复杂的,应该考虑到多方面的影响。
在我看来,柴科夫斯基的悲情气质,最主要的,是俄罗斯民族悲情气质的集中体现。丰子恺先生认为柴科夫斯基的音乐是非俄罗斯的,更接近西方古典音乐。而斯特拉文斯基却认为他是“最俄罗斯的”。我同意一种观点:俄罗斯地广人稀,冬季极为漫长,又白雪覆盖,造成不同地区、村落之间交流的困难,使人们在一年中很长时间里,封闭在一个相对孤立的环境中。即使是城市,漫长的冬季与城市周围茂密的森林,皑皑白雪上偶尔见到孤单的小鸟等等,也形成一种压抑的自然环境,形成了俄罗斯人所具有的肃穆伤感、凝重忧郁的悲情气质,这种气质缺少含蓄、容易狂放、粗暴,也会导致多愁善感、脆弱和悲观。《第六(悲怆)交响曲》充分表现了柴科夫斯基的悲情气质,也是他总结性的代表作。
曾有人把柴科夫斯基与我国唐代诗人李商隐对比,认为他们之间有相似之处。相似在何处?如果从人品上说,李商隐尽管诗写得好,可在牛李党争中朝秦暮楚,名声臭得实在要命。柴科夫斯基是断无这个问题的。就性格上说,两个人也说不上有相似之处,李商隐的郁闷和压抑,与他在官场上的作为有直接关系。而在艺术表现方面,虽然他们的作品都曲折表达着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失望情绪。但作曲家的意图是表达,诗人的意图却是隐——写了许多无题诗。尽管“隐”也是一种表达,但却让人去猜,在作者那儿,估计你怎么猜也猜不对。李商隐的诗如同其名字,商者,伤也。可他却要把悲伤隐藏起来,不直说。商隐者,伤隐也。商,是中国古代五音之一,与秋在五行中同属金,商声也就表示哀伤、凄怆的声音,如秋季寒风肃杀之声。这点,柴科夫斯基的作品也是如此。但李商隐的诗表达的最多的是无奈和失望,而柴科夫斯基的《悲怆》则带有痛苦和绝望,这在作品开头就已昭示出来。其实,未必李商隐的心情会比些科夫斯基好些,大概是诗词与音乐有关不同的表现特点,诗总比音乐含蓄。
浪漫的性情多带有悲情色彩,浪漫的人总是多情的,可“多情却被无情恼”几乎带有规律性,所付出的情感、所抱有的期待常常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要求。李商隐虽然多情,但由于政治上的投机行为,弄得自己一生颠沛流离,而柴科夫斯基又过于多情!我想到另外一个人,就是苏轼的妹夫秦观。秦观与柴科夫斯基两人性格特点极为相似,都非常敏感多情,都具有忧郁的气质情怀,都在现实面前表现为极度的痛苦和绝望。秦观面对在朝廷被排斥、一再遭受贬谪远徙,在他的一首《踏莎行》中倾吐了他的凄苦失望:
雾失楼台,
月迷津渡,
桃园望断无寻处。
可堪孤馆避春寒,
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
鱼传尺素,
砌成此恨无重数。
郴江幸自绕郴山,
为谁流向潇湘去?
秦观的这首词被当时某人(请原谅,记不得是谁了)看到之后,惊诧的说:秦观将不久于人世矣!结果两年后,秦观51岁时抑郁而死。
柴科夫斯基的《第六(悲怆)交响曲》也同样表达了这种心情,这首交响曲也不幸成了他的绝唱。在作品首演成功第二天,其弟弟把该作品起名为《悲怆》,结果相隔不到十天,柴科夫斯基因感染霍乱不治身亡,时年53岁。
李商隐呢,他的那首《锦瑟》诗也是他本人的“天鹅之歌”: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首诗约作于公元858年,不久,李商隐就在他的家乡河南荥阳抱恨离开了人世,他只活了47岁。
这三位都死得太早了,否则会有更多的好曲、好词、好诗留给后世!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尴尬和无奈的时候,这些尴尬、无奈,有时是因为自己经历尚少,缺乏历练。前几年,有一次郁闷得很,顺手翻一本胡云翼先生编的《宋词选》,看到秦少游的《踏莎行》,一时感慨,也照猫画虎的模仿一番:
夜伴寒星,
人在野渡,
百年未半心如暮。
世态炎凉怎奈何?
桃园望断无寻处。
往事悠悠,
心底情愫,
翰海茫茫谁与诉?
驼铃单调空野低,
寂寞孤独行者路。
这肯定不是我的“天鹅之歌”了,呵呵!因为时间过去好几年了,再说我比他们三人豁达!
去年,我送女儿去上学,独自一人坐在饭馆,想起以前在此地的经历,又发了一通感慨:
已了情缘空遗恨,
昨时故旧更不识。
岁月沧桑心已老,
其中苦辛又谁知!
金菊欲艳逢秋去,
弱柳白头正春时。
襟抱未开酌酒冷,
他乡独坐吟小诗。
写完,用手机发给朋友。朋友惊讶:真的如此伤感?我说:古人作诗多无病呻吟,我为何不可?
张中行先生认为,词的正宗应该是婉约而非豪放,既表达人的“幽微之情”。那种既不是婉约又不豪放的议论诗,张老更不欣赏,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老先生说,这样的诗,居然进入小学生课本,真不知编教材的人是怎么想的。这话好像很有道理,因为只有这种“幽微之情”包括悲情,才有丰富的语言去描述、去表达、去发泄、去体会。而且,真正的人生,一般都带有悲情成分,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对人生和社会,那种革命的乐观主义或是革命的浪漫主义是有害的,当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浪漫主义与权力结合的时候,就会产生灾难,“大跃进”就是如此,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现在想来,是多么荒唐!
柴科夫斯基、李商隐、秦观还告诉我们,无论科技如何发达,人类最难做到的是与自身和平共相处,他们那个时代是如此,我们现在也是如此。随着科技不断进步,热兵器代替了冷兵器,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国与国难以和平相处;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安全感等并没有增加,甚至在减少,人与人也难以和平相处。人的痛苦、绝望、无奈、苦闷、不安心情不是来源于自然,而是社会。
|
评分
-
查看全部评分
|
 京公网安备 11010602010207号
( 京ICP证041102号,京ICP备09075138号-9 )
京公网安备 11010602010207号
( 京ICP证041102号,京ICP备09075138号-9 )